暴走武侠任我行人物评价,他原是个令人心折的人物,连令狐冲也觉得他谈吐豪迈,识见非凡,确是一位生平罕见的大英雄、大豪杰,虽然先前见他对人手段未免过分毒辣,但倾谈之下,便渐渐相信英雄处事,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。其魅力可以想见。

他并不只是一个武艺高强的邪教教主,而实在是个不平凡的人。在西湖底一困十二年而保存理智雄心,显见耐力之强;一脱困便着手恢复教主地位,短短时间内取得优势,显见手段谋略高明,他对少林寺方证大师说出他“佩服的三个半人物”,头一个便是夺他位、囚禁他于黑牢中的东方不败,又以武功高而“心地慈祥,为人谦逊”之故佩服方证大师,显见他胸襟识见不凡。这人虽然叫做“任我行”,名副其实的自大狂妄,专横骄做,却不是只一味自大。任我行的城府之深,见于他故意把“葵花宝典”送给东方不败,引他沉迷其中,他对人性反应了解之深、计算之准,也算惊人了。
但是以这样不平凡的一个人,最终还是掉入最庸俗的陷阱:他自己鄙视东方不败弄出来的一套肉麻歌功颂德的规矩,但一旦自东方不败手中夺回大权,很快便改变心意,对下属的谀词十分欣赏,比东方不败犹有过之。
他初次重上黑木崖,听见上官云跟他请安,说什么“教主千秋万载,一统江湖”,但到后来,他称雄称霸,率教众到华山之巅,要五岳派向他臣服,上山之时鼓声号角声吹吹打打,又有一大堆人齐声呼喝道:“日月神教文成武德、泽被苍生圣教主驾到!”俨然是皇帝驾临的声势排场,也就是跟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排场大同小异。
但是,两个故事有一个分别,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,就是“权力使人腐化”的寓意,在 《笑傲江湖》十分清晰,在《天龙八部》则不见。
任我行打败了东方不败之后,在黑木崖上接受教众札拜,任盈盈走了出去,跟令狐冲说,她觉得一个人的武功越练越高,名气越来越大,“往往性子会变”,虽然他自己不知道。
失势的任我行讨厌人奉承,但夺回权力之后便变了,这就是权力的腐化作用。令狐冲自是憎厌奉承制媚的言词,他的看法,更加深入,就是这种行为,其实对双方都是侮辱:“言者无耻,受者无礼,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,自己更加无耻。这等屈辱天下英雄,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?” 不过,《笑做江湖》到底是宣扬侠义英雄理想的一部小说,大凡违背这种理想的行为,金庸都透过各个人物之口,加以批评,但现实世界当然不是这样的,现实世界讲的不是理想,而是成功之道,而小人物的成功之道,往往是靠大量的吹牛皮、拍马屁,《鹿鼎记》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,因此就不大谈理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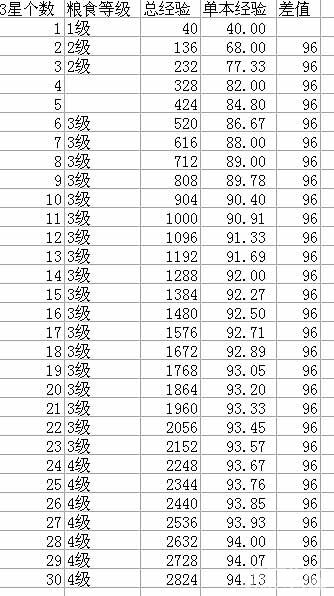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关注游戏狗订阅号
关注游戏狗订阅号